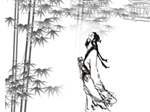正因为如此,理解《乡土中国》,局限于文本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将眼光投射到历史的纵深处,投射到现实的大空间,在不同的维度去发掘它的内涵、价值与意义。
《乡土中国》从“乡土”入手,揭示了乡土社会的“超稳定”特征。小农经济将广大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一生一世,祖祖辈辈,这样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那就是“熟人社会”。历史一页一页地翻过,但并未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产生新的内容,增加新的要素。有历史学家称这种“超稳定”的历史是“没有时间的历史”,千年如同一年,一年遮蔽千年。考虑到几千年来,传统中国的生产方式、价值理念与社会形态的延续性与同质性,用“超稳定”来形容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段,不算夸张。
这个田园牧歌式的历史终结于1840年,鸦片战争让中国社会发生了断崖式的变革。晚清重臣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命题,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是从边患与国防的角度界定这个“变局”的,但此命题却被人们广泛接受,其所指也远远超出了国防的范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生活习气,无不涵盖其中。
传统中国的迷梦在洋枪洋炮的硝烟中惊醒。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那几代中国人,大概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震惊与迷茫。
近代中国人的“突围”从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是“开眼看世界”,另一个我姑且称之为“反身看自己”,二者难解难分,互为动因,彼此纠结,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与心态。近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与艺术,无一不带有这种纠结的痕迹与创伤。
“开眼看世界”,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在“学技术”。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师夷长技以制夷,虽属被动,却也自然。但学技术这条看起来便捷易行的康庄大道,最后梦碎于甲午海战。第二阶段是学制度。近代人试图模仿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但这条路最终幻灭于辛亥革命。这些尝试宣告失败,就有了第三个阶段,有人称之为“学文化”。为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我称之为“文化的对话与反思”。学技术,不行;学制度,也不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不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不行?这个发现让人震惊,可算撕心裂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一直充满自信,即使在屡战屡败的绝境下,也还有最后安身立命的港湾,那就是悠久的文化与深厚的传统。事实上,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整合与激励效应。总体看,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撕裂性的冲突更少。即使发生了,也都能很快地自我修复与弥合。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是这样造就的。但在近代,中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让古今之间的和谐关系受到强大冲击。《狂人日记》里那句“名言”似乎也代表了“今”对“古”的质疑:“从来如此,便对么?”
说到底,“反身看自己”与“开眼看世界”之间,有着复杂的因果关联——那些“开眼看世界”的人,往往也是“反身看自己”的先知,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无不如此。理解《乡土中国》也需要回到这样的历史纵深处观照,这是费孝通“开眼看世界”之后“反身看自己”的产物。总体上,可纳入他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探索范畴。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命题。他回忆说: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没有文化的自知之明,仅仅按照传统的惯性生活,这样的民族是危险的;处在弱肉强食的近代丛林世界,缺乏文化自觉的民族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中国近代的屈辱与辛酸,不能不说与文化自觉的缺失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1944年,费孝通出访美国。面对生机勃勃的美国社会,费孝通痛感中国传统文化之保守。他将传统文化比作“生了硬壳的文化”,不无痛惜地写道:
费孝通绝非妄自菲薄之辈。他在繁荣的美国社会后面,也看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以及它必然带来的资源匮乏与紧张的社会关系。这让费孝通又看到了中国式的知足常乐的人文价值。
在《初访美国》中,费孝通写的是美国,萦绕于心的依然是他的祖国;表现在文本上,就是它隐含的中西(美)对比的思路。这样的思路也同样存在于《乡土中国》。不同的是,《初访美国》明写美国,暗嵌着中国;而《乡土中国》明写中国,暗嵌着西洋。比如在《家族》一节,他写道:
有人将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对立起来,似乎水火不容,这不是事实,也不合费孝通的本意。上述这段“附带说明”,不仅出于学者的严谨,而且透露出费孝通在中西对比的格局中揭示中国文化特点的认知方式。可以说,在中西文化的联系与对比中,中国文化的特点才能充分显现,这恰恰是走向文化自觉的必由之路。
费孝通的根在中国,在民间,在乡村。他的学术福地在吴江的开弦弓村,这个小小的中国村庄,成就了他的《江村经济》;全面抗战时期,费孝通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更多的土地,这就有了“云南三村”,即《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乡土中国》的写作,离不开这些田野调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让他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让他对中国乡村与农民有了直接和深切的理解。在他笔下,经常能读到“了解之同情”与理性洞察之下的温情。
费孝通生活在中西古今矛盾最直接、最集中因而也最尖锐的江南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的主旨。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的一个士绅家庭,家庭开明,他上的是新式学堂,接受的是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因为家庭的缘故,孩提时期的费孝通对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似乎并无明显感受。到了1935年,当他来到毗邻家乡的开弦弓村(即“江村”),费孝通真切地看到了中西交通给一个中国江南乡村所带来的影响。他写道:
吴江毗邻上海,那是中国最接近世界市场的近代城市。在世界经济与西洋文化的冲击下,开弦弓村的社会结构正被破坏,生丝业也遭到极大冲击。不过,费孝通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理性的乐观。他坚信:“在它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5]
“一个崭新的中国”,这就是费孝通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他明白,要走出这种“内部冲突”与“巨大消耗”,离不开自觉的、理性的文化反思。《乡土中国》的立意,从根本上看,就是思考传统文化的“根”在何处,我们从何处而来,我们究竟应该往何处去。
“何处来,何处去”,这是对《乡土中国》主旨的基本界定。
乡土是传统文化的根。从对乡土的审视,走向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理解与反思,这是费孝通文化思考的基本路径。
《乡土中国》试图给乡土生活与传统社会一个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解释。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一切自然而然,一切都好像天经地义。但是,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文化是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6]这都需要解释。
在费孝通看来,理解这些问题,是走向文化自觉的必经之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意义赋予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因而,我们可以说:反思即创造。
费孝通的解释之旅从“乡土”开始。无独有偶,费孝通对美国文化的分析也是从“土地”开始。他写道:
在费孝通看来,新大陆广袤的土地及开垦自由,锻造了美国人热爱自由、敢于进取的精神风貌,他们的民主政治也与此密切相关。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费孝通的解释思路切中了唯物史观的精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看作“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他说:“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8]在传统中国,“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基于血缘的家族则是“人自身的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土地与家族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理解它们,成为理解乡土中国的关键。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是能将这两个“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关联起来的核心概念,它既是土地所衍生的必然,也是家族运行的必需;既是一种自然秩序,也是一种伦理秩序。经过长期的积淀,差序格局成为国人一种普遍的心理秩序。
差序格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血缘等级制度,“血缘”给“等级”打上了浓厚的情感与伦理的烙印,甚至笼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从此出发,可解释传统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乡土中国》涉及的家族、礼治、无为政治与长老统治等。即使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比如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这些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中,尖锐的阶级对立也往往与血缘伦理纠合在一起,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红楼梦》中,贾府这样的“功名奕世,富贵传流”的贵族之家,与贾氏家族的其他子弟如贾芸、贾蔷等人,构成了一种等级与温情兼在的关系。贾芸尽管卑微贫寒,与宝玉却是叔侄关系,因为宝玉的一句玩笑话,贾芸甚至可以夤缘而上,将叔侄关系上升为“父子关系”。
贾芸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鲜明地反映了差序格局的特点。血缘本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联,客观存在,无可摆脱;贾芸却将这一层血缘关系的外延放大,将它引入自己的经济生活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而他的街坊邻里也认为理所当然。这样,血缘就走出了家族,进入社会生活。换句话说,它从一个实在的伦理法则转化成为一种虚化的社会观念。这一点,连乡下文盲刘姥姥都心知肚明。她敏锐地发现了女婿王狗儿家与王夫人家的关系,并利用这个关系进入贾府,成功地从一个乡下婆子晋升为“姥姥”。黛玉说“她是哪一门子的姥姥”,并没说错:王狗儿家与王夫人家除了同姓一个“王”字,本来就没什么血缘关系。可见,血缘超越了血缘本身,成为社会交往中的一个桥梁或工具。
从贾芸到刘姥姥,可清晰地看到一条血缘不断稀释而血缘观念却不断泛化的演进线路。这是一个从自然伦理向文化观念的转化过程。从乡土社会的生活习惯到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积累与繁衍的过程,而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则提供了必要的时空保障。言行经反复而成为习惯,习惯因积累而成为习性,习性因积淀而成为文化,文化因传递而成为传统。
源于乡土社会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成为儒家文化生长与发育的肥沃土壤。儒家文化的根基正在于血缘伦理。《论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儒家政治与道德秩序的建构逻辑。“孝”乃为人之本,归根到底也是政治秩序之“本”。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儒家典籍中的很多矛盾。譬如在《孟子》中,舜善待他的父亲瞽瞍与“日以杀舜为事”的异母兄弟象的故事,就颇让人费解,尤其是大舜善待象的逻辑:
圣王大舜是宽厚仁慈的代表,对心怀奸险的弟弟,也能“亲之”“爱之”。但问题是,大舜不仅是象的兄长,他还是天下的首领,他的威望正是在“诛不仁”中树立的。“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他的公正体现在哪里呢?只能说大舜是公正而有私。现代人觉得荒谬的行为,儒家却引以为傲,且认为理所必然,原因正在于儒家的立论前提是家国同构,国就是家。这样,孝子与忠臣、孝悌与忠信、齐家与治国,便达成了逻辑的一致。
儒家道德理论亲切而素朴,它关注的就是人,就是身边的人,首先就是血缘意义上的父母与兄弟。做到这一点,便立定了“根”,就可以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了——而推己及人就足以“平天下”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推演的逻辑无不如此。费孝通以“推”字来概括儒家文化的建构逻辑,抓住了儒家文化的根本。
儒家追求的道德境界很高,但给定的起点与路径却很“亲民”,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当然,小事不小,小中有大,所有的“大”都在这“小”中了。所以,人皆可为尧舜,就看你愿不愿意,看你够不够坚韧。
在大舜对待兄弟的事件中,也可看出儒家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即标准的“伸缩性”,转圜与解释的空间很大。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公私不明,群己不分,界限模糊。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学术思维。即使是相对超越的哲学范畴,正如费孝通说,《论语》的核心概念“仁”,孔子的解释也是虚实不定,总给人不好把握的飘忽感。
费孝通从“乡土”出发,从生产方式到社会结构,再到社会的治理方式,最后延及社会的内在矛盾与变迁,在因果关系的梳理中构建乡土社会发生与运作的逻辑。如果乡土社会是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个假设前提是成立的,那么,很多传统经典著作都可借助《乡土中国》的这套理论来解释。前述《论语》只是一例。再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为什么要用“结义”来表达他们“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志向与情谊?《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也讲究一个“义”字,但局限在群体内部;对群体之外的人,却未必厚道。如何解释他们的行为逻辑?《红楼梦》写的是贵族之家,但它的运行逻辑却与《乡土社会》所揭示的家族文化高度吻合。缘何贵族之家也有“乡土本色”?这些作品构成了《乡土中国》教学的重要资源。《乡土中国》与众多传统经典的这种“互文”关系,正彰显出这本学术性著作的强大解释力和不朽生命力。
在《乡土中国》的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偏颇:似乎掌握了《乡土中国》的解释逻辑,就可解释中国社会的各种现象与事件。在笔者观察的课堂上,有老师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可以诉诸公堂的事情,当事人往往更倾向息事宁人”这样的问题,学生多借助“无讼”的文化心理来解释。这种简单的贴标签与套用,不仅违背了学术阅读的规律,也可能遮蔽了问题的本质。在现代社会,法律观念深入人心,如果人们对司法有足够的信心,恐怕还是愿意对簿公堂的。考察现实生活,首先还得在现实矛盾中梳理它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而不是直接、简单地归结为某种文化心理。文化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是深刻而持久的,但往往也是间接的。直接归因,可能会转移我们的视线,甚至因此而忽略了对现实的批判与改造。
这样的偏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夸大了《乡土中国》的解释力。作为一部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对传统社会的解释有其特定的学科视角与视域,但也因此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社会学的解释不能取代政治学的解释。像鲁迅,也致力于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反思,但因更着眼于社会政治的现实考察,他更多看到隐藏在文化心理后面的乡土社会复杂的利益冲突、统治者对民众的愚弄与剥夺,表现出迥异于费孝通的思路与风格。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近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尤其是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费孝通作为“模型”的传统社会存在着天壤之别。可以说,如果不能发现《乡土中国》与现实生活的关联,说明学生还没有走进文本;但如果不能发现《乡土中国》与现实生活的区别,则可能犯了简单化、机械化的错误。因此,阅读《乡土中国》,不仅不能随意跨越学科的边界,还要始终保持理性的思辨精神,辨析《乡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的复杂性。
家族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正因如此,在现代社会运行中,它的衰败与式微也是不可逆转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家族及其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批判礼教,可它选择的靶点却是暴露“家族制度”的弊害;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尖锐地指出,孝悌之道就是家族伦理和专制政治之间的根基;李大钊则态度鲜明,抨击“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源,都在家族”。“五四”之后的一大批家族小说和戏剧,主流意见都是揭露和批判家族的罪恶,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等等。
家族的身影正在远去,是不是意味着它的基因也消逝了呢?高考作文命题是考察时代观念的一个窗口,如2015年高考语文新课标全国甲卷作文题:
有人认为小陈大义灭亲,有人认为她违背孝道。但材料提供的事实显然不支持这样的判断。命题给“事件”设定了一系列的情境因素,比如“总是”“屡劝不改”“迫于无奈”“更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通过微博私信”等,这些因素将“女儿举报父亲”的背景、动机、原因、方式做了全方位的“合理化”,而“举报”所可能带来的家庭伦理风险与社会道德风险也因此抵消。事实上,在这个具体的“举报”事件中,女儿的目的旨在父亲及家人的安全,显然谈不上“大义灭亲”;而“举报”也是在穷尽了一切合理手段之后的无奈之举,且利用了“微博私信”这样相对体面的方式,说小陈“违背孝道”也不合事实。
出现审题偏差,不能简单归结为审题者的粗心大意,恐怕更多源于学生头脑中自觉不自觉的观念束缚,这就是传统的“孝”与“隐”的观念。正是在这个传统文化心理的作用下,考生丧失了独立思考与自主辨析的意识,在思维惯性的引导下陷入了审题偏差。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孝”跟传统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孝”是以剥夺子女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自由为前提的,现代意义上的“孝”强调的是对长辈的尊重与关爱,与独立人格无涉。至于“隐”,即使在古代,它与国家法律、公共秩序之间的矛盾也是极为尖锐的。《史记·循吏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为了忠孝两全、情法兼顾,石奢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足见“隐”的沉重与煎熬。在现代社会,“孝”与独立人格是有冲突的,应该限定它的具体内涵;“隐”与公民身份是有矛盾的,应该厘清其法律边界。
在今日之中国,公民的独立人格与法律的基础地位已经深入人心,“孝”与“隐”基本不再能羁绊我们的现实选择。但在精神深处,这些传统观念却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可以说,《乡土中国》对于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已远不如前,它的价值更在于引发我们对自己所存身的这块土地的文化回视与反省。
站在社会发展的潮头,赋予《乡土中国》以当下意义,这也是一种“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539-540.
[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3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0:246.
[3]费孝通.乡土中国 乡土重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41.
[4]费孝通.江村经济[M]//费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73.
[5]同[4]267.
[6]同[1]75.
[7]费孝通.初访美国[M]//费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35-436.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7.
[9]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01.
[10]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864.
——《语文学习》2022年第9期
联系客服

微信登录中...
请勿关闭此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