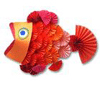曾熙 篆书作品。曾熙曾有多件传世作品题跋为“以蝯叟(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法……临此”
来源 | 《中国书法》2022年第3期
作者 | 余惟杰、谈晟广
原题 | 书画同体:金石学脉络中的曾熙及其核心书画观
分享 l 书艺公社(ID:shufaorg)
清末民初书画家曾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海上艺坛有“艺林泰斗”之誉,其晚岁以金石学“书画同体”之观念作画,有较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曾熙置于晚清民国的金石学脉络之中,揭示其“书画同体”观的形成,以及所受碑学运动以来以“篆籀”为核心的“追本溯源”艺术观念的影响,同时结合中国画复兴运动的时代语境,探讨其“书画同体”观的发展与演变,进而揭示其对画坛与艺术史的影响路径。作为民国初年沪上书画家中的佼佼者,曾熙(1861-1930)与他的至交——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李瑞清(1867-1920)并称“南曾北李”,名动一时。曾熙早年曾参加科举,为光绪癸卯(1903)科进士,特旨授兵部主事,后绝意仕途,长期主讲于湖南的书院。1915年秋,曾熙前往探望辛亥革命后退居沪上的老友李瑞清,为其所挽留,从此定居沪上,鬻书授徒,走上一条与前半生迥异的道路——职业书画家。时代风云变幻之下相对被动的身份之转,却意外地成就了曾熙在二十世纪初期较为煊赫的艺术声名 。
曾熙、李瑞清,与吴昌硕、沈曾植、黄宾虹诸人, 曾共同辉映海上艺林。然相较于吴、黄,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曾熙的身后名却经历了长期的岑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有研究者陆续关注到曾熙,研究多以生平、书风介绍为主,有研究者将其推为“民初四大书家”之一,[1] 同时亦不乏批评之声。[2] 2010年,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的老师:曾熙、李瑞清书画特展”,该馆馆长张誉腾在图录的序言中写道:“曾、李二氏俱为清末重要之书家人物,成就不容小觑,而罕为今人所知;他们也给予近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很大的熏陶与影响。”[3] 作为“张大千的老师” 的曾熙,逐渐进入更多的研究者视野。从曾熙的艺术生涯来看,曾熙晚年重点所在的绘画活动,相对较少有人关注。[4] 谈晟广则指出,曾熙晚岁以书家本位意识作画、主张“以书入画”的“书画同体”观,是其核心艺术观之所在。[5] 不过,要更深入地了解曾熙“书画同体”观的形成,则需将其置于晚清民国以来的金石书画谱系之中,故本文拟回归金石学脉络中,梳理其“书画同体”观的生成与演变情况,并进一步探究其“书画同体”观的影响路径 。曾熙(1861-1930),衡永郴桂道衡州府(今衡阳市)人。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俟园,晚年自号农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是海派书画领军人物,一生都专心致力于古代书法的研究和创作。
纵观曾熙的艺术生涯,有两个重要的转折:1915年,前往沪上探望老友李瑞清,为老友所挽留,自此客居沪上鬻书,成为职业书家;1923年,时年六十二岁的曾熙自订《曾农髯先生鬻画直例》,正式以职业画家的身份示人。这两次转变,从当时的影响和反应来看,均是成功的:1917年,书家、金石家张祖翼逝世后,4月6日的《申报》登出《书家寥若晨星》一文,将曾熙推为沪上工篆隶书家中首屈一指者。[6] 1930年,王一亭集其所藏曾熙遗作之精品,汇印成《曾农髯遗墨》,《申报》刊发此书讯,称其“自李瑞清故后,执书画界牛耳几十年”“有艺林泰斗之誉”。[7]晚岁作画,是曾熙艺术生涯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特点。在曾熙为弟子马宗霍所写的《山水册十二帧》后, 有其友人谭延闿、陈三立、夏寿田等人的题跋,均不约而同地提及曾熙“晚岁”作画一事,并给予较高评价。如陈三立对此举由“哂其为蛇足”的不以为然,到“以谓可攀宋元名辈,即余亦无异辞”的认可,并且在曾、 李二人中,尤为推崇曾熙:“农髯与清道人皆以书势名天下,顾皆晚岁始作画。余尝两哂其为蛇足,徒弄狡狯耳。久之,乃愈为世所推重,以谓可攀宋元名辈,即余亦无异辞。盖二子胸中所具邱壑,忍俊不禁,郁积而一吐其奇,所习在意在目不在手,故自然成异境,非余技也。农髯所就或过清道人。”[8]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自称梅花庵道人,喜食蟹,自号李百蟹,入民国署清道人。江西省临川县温圳杨溪村(今属进贤县温圳)人。清末民初诗人、教育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
曾熙晚年作画有两个明显的个人动机:其一乃“悦生娱志”之消遣,其二乃谋生应世之所需。《曾农髯先生鬻画直例》中言:“老髯年来颇苦作书,尝写奇石、 古木、名花、异草,与生平经涉山川之幽险,目中所见世间之怪物,不过取草篆行狎之书势,洒荡其天机耳, 悦生娱志,不贵人知,然见者攫取赍金叩门。”[9] 从公布润例鬻书开始,曾熙便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作书也从超功利的自娱遣兴,转向谋生应世。职业书家无从任性,必须调整自己,以应鬻书者之需,曾熙的至交李瑞清,曾在其鬻书润例中生动地描述职业书家之苦,谓“索书者急于索债”。[10] 绘画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曾熙晚年适性之所在,尝言每执画笔,便有“百虑皆净”之感:“古人称画能颐年适性,予每执笔,百虑皆净,无异身到极乐国,户外一切咆哮之声,不能入耳。”[11]曾熙 浯溪一角图并跋轴 107×58cm 1924年 私人藏不过,和鬻书一样,曾熙晚年作画,进而鬻画的活动同样包含着谋生应世的动机。1929年,在三媳赵氏返湘之时,曾熙曾作山水图赠之,并告以书画谋生之“苦”:“书画乐事,然以之易钱则苦,须知一笔一点皆精神所寄,一钱一粟皆筋力交换得来。”[12] 用以易钱的书画,多少会附着商品之属性,李维琨曾指出,在新旧更替的上海,海派画艺的书法味、金石风在沪上自有其市场,成为以封建士绅、买办新贵、新潮白领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商业文明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13] 从曾熙一些画作题材选择上,可以看到不乏商业迎合之倾向,他有时会选择有着良好寓意的题材,如象征富贵、长寿的牡丹、松树,有时也会利用谐音,如荔枝(通常谐音“万利”),明显有对沪上士绅、买办商人、银行家等为主体的艺术消费群体的迎合。可见,士人与职业书画家身份的两重性,也决定了曾熙晚年作画动因的二重色彩:它既有文人抒情写怀之精神属性,也离不开职业书画家谋生应世之商业特征 。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中国的思想与文化体系日益脱离其常规运行轨道,传统中国画亦面临价值危机。一九一七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批判写意文人画之弊端,认为绘画不是单纯的笔墨游戏,强调绘画的写实主义。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来看,曾熙之所以在此际公开以画家身份示人,并且将晚年主要精力转移到绘画上,当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绘画领域的“保存国粹”思潮影响有关。1920年,金城、陈师曾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在沪上,则有上海书画研究会、青漪馆书画会、上海书画会、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等书画社团涌现,这些社团大抵均以“保存国粹”为旨归。作为一个传统艺术家,曾熙自然也无从置之度外,从他这一时期参与的社团活动、社会活动也可看出他的倾向,如参与钱病鹤在1922年成立的以“挽救国粹之沉沦,表彰名人之书画”为宗旨的上海书画会的活动,其自书隶书联“奇文共欣赏,澹意得长年”刊载于该会刊物《神州吉光集》第三期(1923年4月版),他还是停云书画社的一员。《曾熙年谱长编》中,特别注意到曾熙鬻画与“国画复活的运动”时间节点之关联,并且指出“本年谭延闿就注意到谱主作画甚多,叹为'直追道士矣'。下面将可看到,停云书画社开会成立时, 谱主是其首批成员之一。上海书画会和停云书画社都是国画复活运动中成立最早的中国书画社团,于兹显示谱主介入1920年代书画活动的愿望,也许可以说,弟子张大千,张善孖、马企周等,都是他带入上海画坛的。”[14] 从曾熙晚年的活动来看,这一观察颇具合理性。在所谓中国画“保存国粹”运动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关于“文人画”价值的认识与发掘。1921年,“京派”代表人物陈师曾发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 针对当时以“写实”改良中国画的主张,指出“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意图发掘文人画的现代价值。[15] 陈师曾关于文人画的主张,在当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回响,如何认识、发掘“文人画”的价值,成为保存国粹命题中的基本之义。从曾熙晚年的艺术活动来看,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文人画“书画同体”观的参悟与践行之中,正体现了他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与主动回应 。陈师曾(1876-1923),原名衡恪,字师曾,号朽道人、槐堂,江西南昌义宁(今江西修水)人,近代著名美术家、艺术教育家。
中国艺术史关于“书画同体”的探讨由来已久。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开篇“叙画之源流”中强调中国早期文字与图像起源的同一性,他首先将文字(书)与图绘(画)视为传播天命的媒介,此二者“异名而同体”或“同体而未分”,并不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而指出在书、画从“同体”走向分化后,又因二者在后世表达工具(毛笔)上的相同,拥有了相同的笔法,即所谓“书画同笔同法”。十四世纪初期,赵孟頫将“书画同源”发展成为“文人画”一个独特的文化特征,强调“以书入画”,他创作了《秀石疏林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并自题:“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16] 明清以后的文人画受其影响,亦往往直接与“写”相关。赵孟頫 秀石疏林图(局部) 27.5×62.8cm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以来,金石学的兴盛促成了清代中晚期的碑学运动,咸同以后,碑学已呈一统天下之势, 此际的碑学书家亦自觉以“书画同体”的眼光,试图融金石笔法于绘画之中,出现了以碑学书家为主体的“书家画”现象,文人画“书画一体”传统相应发生重大转变:“以书入画”的基础——“书”,由以“二王”系统为核心的“帖学”逐渐转向“碑学”,而“以书入画”则呈现出新的阶段特点“金石入画”。曾熙的“书画同体”观正是在金石学谱系之中形成的,其形成原因,可从两方面考虑:其一是对碑学运动以来的“书家画”强调“笔法”传统的总结与取法;其二则是以“金石学”的眼光创造性地继承古典绘画传统。从曾熙1923年发布的鬻画润例中可以看到, 他在强调自己“以书入画”的作画特色的同时,重新勾勒了“以书入画”的文人画谱系,除了人所共知的赵孟頫、米芾的“以书入画”,晚清两位以书法名世,而以绘画为余事的金石书家——何绍基、翁同龢,进入了他的视野之中:以书论画,髯之所画,古人尝先我为之矣。昔者与可观东坡墨竹,惊为太傅隼尾波书。米襄阳尝曰:予点山苔如汉人作隶;赵松雪写枯木竹石,题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近世蝯叟兰竹、松禅山水,其画耶?抑书耶?道人既殁,将与天下能读髯画者质之。[17]
曾熙在绘画题跋中也多次提及何绍基,如曾熙曾作五松五梅花卉扇十帧,在题跋中他两度提及何绍基,一云:“直是鼎彝变相耳。道州七十后傥画梅,当有此风骨。”一云:“以道州笔写马遥父松法。”[18] 曾熙还在自题写梅诗中,将何氏篆书与梅花虬曲的枝杆相比拟:“不写齐罍写梅花,璆枝缭曲任参差。平斋两拓蝯翁篆,恍惚苔深落照斜。”[19] 这样的反复强调,显然自有其用意 。
清代中期以来,碑学运动的主力如阮元、包世臣、 何绍基等书家尝试融金石趣味于绘画之中,尽管“金石入画”的尝试随着金石学的兴起时或有之,而“书家画”蔚然演成一时风尚,则与碑学运动的影响密不可分。[20]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年的黄宾虹将视角投向道咸以来的金石家的“金石入画”活动,提出了其著名的“道咸画学中兴”说,黄宾虹晚年反复指出“道咸画家”群体的特点在于知究“笔法”,并且认为这一“笔法”正是从金石书法中总结而来:“金石家者,上窥商周彝器,兼工籀篆,又能博览古今碑帖,得隶草真行之趣,通书法于画法之中,深厚沉郁,神与古会,以拙胜巧,以老取妍,绝非描头画角之徒所能摹拟。”[21] 在他看来,知究笔法以“通书法于画法之中”的“道咸画家”,正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他曾在与王伯敏的信中,赞赏日本学者大村西崖《中国文人画之研究》的考据功夫,却遗憾对方未能得见“道咸画家”:“考据颇精确,惜未能见中国道咸间之文人画,故未能周全”。[22] 黄宾虹这种基于金石“笔法”角度重构文人画谱系,以回应“文人画之价值”问题的尝试,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其交好的曾熙的晚岁书画活动中已可闻先声 。[23]其内容为:子久山水,外间流传,本耳。惟内府册子与倪迂合装,确是真迹,盖从破碎中含有刚健之气。论黄子久画。吴仲圭从董北苑出,董之点如晋人作书,雍容出之。吴则淋漓奔骤矣。读梅花道人山水长卷。黄鹤山樵世多传其小笔,惟白鹇道人所藏诗书画一轴,松则满纸风声,山亦疏逸见天倪。论叔明。麓台云:今人但以枯笔一二为得倪迂法,不知倪迂从董巨来,其笔所不到,具有绝大力量。麓台论云林画一则。癸亥冬十月,农髯曾熙。曾熙对何绍基等道咸以来碑学书家的“书家画”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其以篆籀为核心的金石笔法的关注上,正如他所强调的“道州笔”,关注在“笔”,而不在“画”。1923年8月,曾熙弟子张善孖前往沪上拜谒曾熙,请教书法与画法,曾熙于此明确指出“书画一原”的基础在于以“篆法”为核心的“笔法”:古人称作画如作书,得笔法;作书如作画,得墨法……以篆法言之,书家笔笔皆画法也;以笔之转使顿宕,究何异写古松枯树。古称吴道子画人物为莼菜条,即篆法也。篆法有所谓如枯藤,画法也。神而明之,书画一原,求诸笔而已矣。离笔而求画,谓之画匠,离笔而求书也,谓之书吏。[24]
这一归本于“篆法”观念的形成,深受阮元、何绍基等碑学书家“溯源返古”的碑学理念影响。清代金石学兴盛,金石家对于金石碑刻的寻访、收藏,使得大量钟鼎彝器、碑碣石刻得以进入书家视野,也使得金石书家得以从更古老的源头溯源篆隶书风,进而获取一种所谓高古的书法气质。阮元的碑学理论中有着强烈的“尊碑抑帖”倾向,所标举的亦正是“篆隶”遗意,在书法上主张“溯源返古”:“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25] 这种“溯源返古”意识,在明末书家中已可看到,如何绍基推崇的傅山,同样强调“溯源返古”,主张从字体的演变源流来探究书法艺术:“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26] “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27] 不过,傅山等晚明书家所长并不在篆隶,直到碑学运动以来,这一从篆隶书体“溯源返古”的观念才在理论与实践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曾熙、李瑞清所推崇的何绍基,正是这一观念在实践上的集大成者。何绍基在学书路径上,强调学书当以篆籀为根柢:“真行原自隶分波,根矩还求篆籀蝌。竖直横平生变化,未须欹侧效虞戈。”[28] 他从大量的周秦两汉金石材料溯源返古,探寻篆籀、篆分笔意,这一取法周金汉石的尝试,也被视为何氏书法成就之所由来。曾熙及其友人李瑞清均延续了这一主张,如李瑞清有言“余书本从篆分入,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乃得佳耳”[29]。曾熙同样强调学书路径,当以“篆”为先:“学书当先篆,次分,次真,又次行。盖以篆笔作分,则分古;以分笔作真,则真雅;以真笔作行,则行劲。物有本末,此之谓也。”[30]曾熙 南岳结庐图并跋轴 133×48cm 1923年 家属藏于书法实践中总结的以篆分笔意为核心的金石笔法,构成了他们书法上试图融通诸体,进而达到“通书法于画法”的“书画同体”的技法基础,如何绍基晚年寄兴兰竹、山水画的活动中,可以看到这位碑学书家自觉“金石入画”的探索意识:咸丰七年(1857)的一首自题画兰的诗中,何绍基表示自己对此艺“忽有所悟”,而其“所悟”,正是“以书入画”:“学画兰花不到家,无端字里尽兰花。今宵走虺奔蛇笔,窜入幽丛乱发芽。”[31] 在同年另一首《画兰》诗里,何绍基揭示了画兰与篆籀笔法的相通之处:“幽兰生性无常格,非叶非花古籀书。颇欲出奇钱郑外,尽情挥洒看何如?”[32] 重庆市博物馆藏何绍基所作《赠吴子俊纨扇》、湖南省博物馆藏《墨兰》扇面,均为何绍基晚年墨戏之作,两作构图大致相似,一丛墨兰从左下角延伸开来,兰叶的笔触老辣,颇具金石气味,《赠吴子俊纨扇》 中,兰花的用笔圆厚,尤具篆笔意味。清代中晚期的碑学书家这种强调金石笔法的绘画实验,虽不成熟,但仍深深地启发了同为碑派书家的曾熙及其友人李瑞清的进一步探索。李瑞清曾有意识地将金石笔法融入绘画之中,在其《画佛跋》中,自道乃以“武梁祠壁笔法”“钟鼎法”写佛像:“余不知画,近颇用武梁祠壁笔法写佛像,大为当世赏鉴家所欣赏。” “以钟鼎法敬写达摩像一躯,下笔真如虫蚀叶也。”[33] 曾熙则一再强调自己作画的特点,在于以“篆分”入画:如1922年,为弟子姚云江写《柏石图》横幅, 直云笔下苍莽之柏石,乃其“篆分”之蜕形:“苍苍莽莽,柏耶石耶?云江弟学吾篆分,其亦知此乃吾篆分之蜕形耶?”[34] 如其《醉写红梅图》,老干有篆笔之圆厚,细枝则深得行草书笔意连绵之势,一气写成,气脉贯通,而其题跋也在强调金石笔法入画的特点:“醉写齐罍又梅花,篆精草意认参差。夅丘有侣还相约,疑是丹成照赤霞”。[35]曾熙 仿石涛泼墨山水图并跋轴 110×60cm 1924年 私人藏从金石传统中总结的“篆法”,也成为曾熙诠释古典绘画传统,进而“入古出新”的基本路径。如他在对元代倪瓒、黄公望文人画传统的师法上,特意强调自己与“奉常祖孙”王时敏、王原祁的差异在于笔法,所谓“笔之来源各别也”:“髯但秦汉篆隶其奔赴腕下者,亦非有意求深厚,其与王奉常祖孙异者,笔之来源各别也。”[36] 他仿古人设色、构图布置,但在用笔上,则独以自家所体会的“篆法”为之,如在他所作《松竹》题跋中,他亦特意点明了自己与八大笔法、墨法之不同:“八大从倪黄出,用笔直,喜用折带,干湿同下。髯以篆法行之,故笔曲,以焦墨施之,故骨苍,知者勿混入八大也。”[37] 1924年以蒋廷锡法作《牡丹苍松图》,自道“但法其布置”,而在用笔上,则“仍以篆草之法行之”[38] 。在一幅《双钩牡丹图》上,他颇为自得地称:“髯不工画,但知以书家笔墨写之,其双勾取宋元法,而以篆分行之,则髯法也。”[39] 此外,曾熙还尝试着以“画法”通“书法”,实现二者的互通,如其为张善孖夫妇所书篆书横批,即自道以“杨补之画梅法临此”。[40] 中国书画的笔墨,历来被视为艺术家“心迹”之呈现,曾熙对“笔法”的强调,实际上也含有对“文人画”内蕴的人文精神的重视,曾熙特别强调笔墨之本,在于操持笔墨之人“气”之涵养:“笔与墨,无情之物也,惟气足以生之。天地之气,赋于人分清浊;人之气,赋于笔墨分雅俗,此言质也。浊者使之清,俗者使之雅,则惟泽之以诗书,蓄之以道德,据德依仁游艺,此其本也。试问以盗跖之心,而欲安弦奏南风之曲,能乎否耶?[41]曾熙 山村图并跋轴 84×43.5cm 1927年 家属藏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金石书画团体汇聚的中心城市,有着相同审美旨趣的金石学家、书家、画家、 收藏家共会于此,他们既是继承与更新中国画传统的核心力量,也是当时沪上最具活力的艺术力量。时人曾将曾熙与吴昌硕、蒲华、高邕、王震、俞语霜、李瑞清、 谭德钟并称“海上八怪”,曾熙的沪上生活常年处于一种沉浸式的金石氛围之中,对金石学“书画同体”的参悟,使其绘画很快形成了特有的风格面貌,也正因此际海上金石之风炽盛,曾熙的绘画很快就被时人接受并且认可,1927年,谭延闿在《为向乐谷题农髯画册》 中感慨去沪五年,曾熙已书画并重,并且认为曾熙成功的原因,正是由于对“书画同体”的参悟:“自余识农髯,初未见其作画,然髯尝语余,谓画稿积胸中,会当一倾写,又谓书画同一源,知书即知画矣。余故不解此,惟惟而已。去沪五年归,而髯之画与书并重,始信言之非虚。”[42]若要了解曾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艺坛的影响,自然不可忽视其作为艺术教育者的身份。自1915年移居上海以后,曾熙便与好友李瑞清一同于此鬻艺授徒,此外,曾熙还先后任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校董、城东女学国画专修科导师等职,育人无数。由于曾、李私交甚笃, 情同手足,且核心书画观念亦大体一致,门下弟子多并列二人门墙。1930年,曾熙逝世后,其门人发起组织“曾李同门会”,在曾李门人之中,如张善孖、张大千、 马宗霍、姚云江、朱大可诸人,均为一时俊彦。金石学“书画同体”观,也是曾熙、李瑞清的核心教学理念。张大千在其《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回顾了曾、李二师分别之于石涛、八大的推崇,并且指出其二师授徒注重“以画法通之书法”:两师作书之余,间喜作画。梅师酷好八大山人,喜为花竹松石,以篆法为佛像。髯师则好石涛,为山水松石。每以画法通之书法,诏门人弟子。予乃效八大为墨荷,效石涛为山水,写当前景物,两师嗟许,谓可乱真。[43]
二十世纪初,在呼吁改良中国画的时代语境中, 原被尊为画坛正统的“四王”传统,因其创作上注重临仿、摹拟古人的复古倾向,受到了猛烈的抨击,陈独秀在1918年发表的《美术革命》一文中指出,要改良中国画,“首先要革王画的命”,认为以王石谷[王翚(1632-1717),字石谷]为代表的王派,大抵都以“临”“摹”“仿”“橅”手段复写古画,有复古,而无创作,对画界产生了较恶的影响。[44] 王派自身因摹古倾向带来的繁琐、僵化的弊病,已呈没落之势,再加之改良国画语境下的冲击,使得二十世纪初期的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原先占据画坛主流的“四王”传统,相应地,被视为“四王”对立面的明代遗民画家“四僧”等开始被发现。贺天健《学习国画六十三年的回顾》一文中即回顾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画坛好尚中“四王”与“八大”“石涛”势力的消长 :我的王石谷、王烟客气息便在这时除得一干二净的。但是接着来的便是粗豪放逸的一种阔笔气派画,就是石涛、“八怪”等在上海抬头呀。不料这风气一开,也成了和四王势力一般的局面,在市上凡气派笔墨不如此便是不好。[45]
曾熙、李瑞清即身处上海这种上升的石涛、八大风尚之中。曾、李的这层偏好,并非是趋时的选择,而是在金石学“书画同体”视野下对于石涛、八大价值的再发现 。曾熙 楷书八言联 180×25cm×2 1926年 家属藏这首先体现在对“书画同体”的技法基础“笔法”的关注上。如曾熙在题李瑞清旧藏八大山人《仿青藤老人墨荷图》时,曾回忆李瑞清教导张大千注意八大“荷柄”即“篆书”之特征:“张生季爰当执贽时,道人诒之曰:八大无篆书,此数笔荷柄即篆书耳。张生尚能记其遗事。”[46] 原系李瑞清旧藏的八大山人《墨荷图》,也被曾熙视为体会“书画同体”的最佳范本,每诏其弟子,学八大必先学此幅。张大千酷爱画荷,一生中留下了大量荷花作品,显然也受二师“书画同体”观之影响,如1975年所作画荷金屏风,堪称大千画荷之精品,屏风右侧写立荷一枝,荷杆圆润、挺拔,起伏生动,气脉贯通,有“荷柄即篆书”的特点,题款则进一步阐发了其师“书画同体”的主张:“花如今隶茎如籀,叶是分书草草书。墨落一时收不住,任讥老子老逾疏。”[47] 张大千 泼彩荷花金屏风(及局部) 1973年 陆菊森家族藏绘画笔法上参以篆籀笔意,风格上离奇变化的石涛、八大,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金石书画家的审美趣味,如碑学运动的集大成者何绍基,即是晚清官员中较早大力推崇石涛、八大,且深具影响力的一位,故宫博物院藏石涛《山水花卉册》,有何绍基、吴云、曾熙的题跋,吴云的题跋向我们提示了何氏对石涛的大力推崇:“蝯书法派本高,论画见解尤超。尝言国朝画家,应推青主石涛。”1926年,曾熙在收藏大家庞元济斋中看到了原为吴云旧藏的石涛《山水花卉册》, 在何绍基题诗的左侧进一步写下了自己对于石涛绘画的理解,并感慨“盖去蝯叟所题将六十年矣”[48],以为呼应。可见晚清民国以来的石涛、八大热的背后,始终笼着一层金石书画家以“金石”眼光对传统的发现与重估视角 。此外,曾熙对石涛的重视,还有对“书画同体”根本精神的探源。在他看来,用以拯“四王”传统之偏的,并非西方的“写实主义”,而是中国画传统之核心——以“写生”为路径的“师造化”精神。而因“黄山”之游,在“四王”“师古人”之外重新激活“师造化”传统的石涛,深深吸引了曾熙。通过比较石涛、八大之不同,曾熙点明了他对于石涛偏好的原因,正在于其从“真山水”上“师造化”的精神:“八大以笔胜,石涛以墨胜。石涛之所以过人,在能从真山水上求之,八大犹不免取倪黄自展其才耳。”[49] 这也是其授徒的关键理念。傅申指出,张大千三上黄山,即受曾熙、李瑞清二师的影响。[50] 而这种影响,主要是对石涛诸人的“师造化”精神的揭示,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云:“又以石涛、渐江皆往来于黄山者数十年,所写诸胜,并得兹山性情,因命予往游。”[51]从艺术成就来说,张大千无疑是“曾李”一门的佼佼者,这一点,曾熙在1919年6月1日写给张大千的信中就曾表示“得弟,吾门当大,亦自喜也”。[52]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八大、石涛热中,张大千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47年,美术史家俞剑华在他的 《七十五年来的国画》一文中将此前七十五年画史分为四期,指出在第二分期,也即民国十六年(1927) 至二十六年(1937)的十年间,上海出现了八大、石涛的复兴时代,并且将此际八大、石涛热归功于张大千、张善孖的推崇、搜求。[53] 尽管曾、李对于石涛、八大的推崇之功,以及对张大千的启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叙事中为张大千盛名所遮蔽,但这也无疑侧面说明了曾、李在清末民初之际,站在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岔道口上,对于路径选择之明智,也即张大千所谓的其师在清末民初之际“一洗旧染,变而愈上”之功。[54]如果按照传统说法,张大千是“立功”,那么方闻则是“立言”。方闻的成就,不同于张大千,是将“曾李”一门中以“金石学”为基础的传统书画学问,结合其所受西方正统的艺术史教育发展而为现代艺术史学科。1959年,二十九岁的方闻联合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艺术史与考古方向的博士研究项目。在普林斯顿期间,方闻培养了数十名中国(东亚)艺术史与考古专业的博士,方闻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分别在北美、欧、亚三大洲的著名大学担任教授,在著名博物馆担任部门研究主管,组成占如今美国各大学中国(东亚)艺术史学科比例多达四分之三的教师队伍,此即西方之中国艺术史学著名的“普林斯顿学派”。此外,方闻教授另一项重大贡献,则是1971年至2000年担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特别顾问和亚洲部主任期间,负责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在这两处建立了除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外最好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系列。方闻(1930-2018),著名美术史家和文化史学家、艺术文物鉴赏专家、教育家方闻教授成功的秘诀,除了在普大又接受了最好的西方艺术史教育并从中得到了“自己本身文化背景中所不可能提供的新途径”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早年跟随属于曾李一门的李瑞清之侄兼得意弟子李健学习书画,深得曾李一门“书画同体”创作观念濡染。李健师教他练习并揣摩篆、隶、草、正“四体书”因结构、章法和运笔差异而产生的四种不同表达体势, 并强调,尽管所谓“四体”的体势会因时代不同演化各异,不过“用笔”的方、圆之法却各体均同。少年方闻赴美的行箧中,便装着李健师在他临走前专门为他创作的四十余幅书画扇面,供他在美期间临习。这些扇面,都是一面书法,另一面绘画,落款中除了诗词之外,往往写有李的书论或画论,这对后来方闻艺术史观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方闻生前在接受访谈时曾表示:“青年时代亲身领受李先生的教诲及其深远的学识,对形成我自己的世界观有难以磨灭的根本影响。我从先师那里首先学会了如何看、触和'感’各种艺术品:书法(多为石刻碑铭文)、绘画、印章、拓片以及善本书等。”[55]2014年,方闻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总结其一生学术的著作— —《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Artas Histo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as One),书中将艺术的历史视为历史本体的一部分,时代跨越两千年,几乎涵盖了传统中国绘画史的全部范围,从笔法与空间形式构建的角度,探究了书法、绘画、雕塑等与同时期其他主要视觉艺术形式的关系。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正是方闻少年时得自李健并且其毕生都在强调的“书画同体”——“书与画皆为历代艺术家所呈现的'图载’,因此'书画同体’的理念将帮助我们迈进那个将艺术化的'状物形’视作艺术家之'表吾意’的中国视觉空间。”[56]这也标志着曾李一脉金石学“书画同体”观,从“绘画”到“艺术史”之总结。在清末民初艺术史的风云变幻之中,曾熙一方面从方兴未艾的金石学传统中汲取养料,从以往的碑学书法经验中,总结金石笔法,在文人画“书画同体”的观念与实践上有了进一步的探索,且以“金石学”眼光, 熔铸古典传统,形成了其独特的面貌,实现了“入古出新”的创造;另一方面,曾熙深入探究中国文人画传统之核心精神,发掘其归本于人、师法造化的精神内涵, 在中国画走到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碰撞的岔路口上,在呼吁改良中国画的时代语境中,冷静地提供了一个颇具启示性的答案 。曾熙 牡丹苍松图并跋轴 133×65cm 1924年 家属藏 在当代庞杂的视觉文化知识体系中,中国艺术尽管依然以继承、扬弃和融合的方式延续,但艺术的本原却时常迷失,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在传统艺术价值体系的“正传”中着手建立起独特的当代艺术价值体系。曾熙及其友人、门人以金石学“书画同体”的视角深入发掘传统、诠释传统的尝试,对于当下艺坛而言,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这种探索,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家对于“自然”与“自我”的持续关注与探索意识,亦如方闻所言:“中国作家们反复申明'书画合一’的信念,而且将这两门艺术的训练看成一个文化人的标志:书与画不仅同样表达了宇宙万物的真正本质,两者还具有共同的用笔技巧。”[57][1]阮荣春,胡光华.中华民国美术史[M].一书将沈曾植、吴昌硕、曾熙、李瑞清列为“民初四大书家”,认为这四人书艺最著,影响最大。参阮荣春,胡光华著.中华民国美术史[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88-91.[2]陈振濂将“曾熙”“李瑞清”“陶濬宣”视为北碑派的末流,称曾熙的书法为“馆阁体的变体”,批评其书“千篇一律”的概念化倾向。参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67-76.[3]张誉腾.馆序[M]//,台北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张大千的老师—曾熙、李瑞清书画特展.台北:台北历史博物馆,2010:4.[4]王耀庭.书家画—曾熙、李瑞清画艺[M]//一文对曾熙、李瑞清画艺有所探讨,文中指出二者技法上以书入画,以及风格上“趋简”的特点。台北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张大千的老师—曾熙、李瑞清书画特展[M].台北:台北历史博物馆,2010:20-29.[5]谈晟广.书画吾老幸有寄:读曾熙画有感[M]//曾迎三编.历代名家书画册页·曾熙.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谈晟广.书画同体:方闻核心书画观溯源[M]//方闻著,赵佳译.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附录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358-366.[6]书家寥若晨星.申报[N].1917-4-6:11.[7]曾农髯遗墨.申报[N].1930-12-29:13.[8][9][12][14][17][18][23][24][34][41][42][46][52]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626,476,696,478,476,696,535,495,456,495,635,616,339.[10][29][33]李瑞清.清道人遗集.[M]合肥:黄山书社,2011:126,158,136.[11][19][36][37][48]曾繁涤.大风堂存稿曾熙书画题跋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150,169,134,133,136.[13]李维琨.海派散论[M]//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海派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271.[15]陈师曾.中国绘画史·文人画之价值[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153-163.[16]关于赵孟頫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参见谈晟广.1300年:赵孟頫的“书画同源”和文人画的新走向[J].文艺研究,2012(5):113-121.[20]万青力指出,清代金石学影响下的书画之变,包含着一个由“书”而“画”的次序问题:“清代书画艺术的深刻变革,毫无疑问地对绘画艺术的时代风格转化,产生了催化作用…在十九世纪中期「金石画派」形成以前,书法上的「碑学」潮流,已波及绘画领域。到十九世纪前期,上述书画潮流对于绘画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参见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9.[21]见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490.黄宾虹晚年强调的“道咸画家”,以书家为主,并反复申说其长处,在于从金石书法中知究“笔法”:“咸同之间,金石学盛,知究笔法,赵之谦、吴让之辈皆有笔墨”“盖以画重笔墨,明人太刚,清代太柔,刚柔得中,惟明季及清代咸同之间有数十人,知用笔之理,从书法而来,上窥金石之奥得之”“清至道咸之间,金石学盛,画亦中兴,何蝯叟、翁松禅、赵撝叔、张叔宪约数十人,学有根柢,不为浮薄浅率所囿”“鄙意清代画以道咸为中兴,如张叔宪、赵撝叔、吴让之皆承包慎伯、何蝯叟而来,翁松禅、陈若木皆杰出。”参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信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219,23,8,320.[22]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信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12.[25]阮元著,华人德注.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1.[26][27]傅山.霜红龛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1037,1058.[28][31][32]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13,520,508.[30]崔尔平.明清书论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455.[35][38][40][50]台北历史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张大千的老师—曾熙、李瑞清书画特展[M].台北:台北历史博物馆,2010:114,179,122,18-19.[39]西南五省文物商店编.艺海钩沉—西南五省(区)文物商店藏品图录选,1991:126.[43][51][54]张大千.张大千先生诗文集卷六[M].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55,55,86-87.[44]陈独秀.美术革命[M]//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29-30.[45]贺天健.学画山水过程自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21.[47]张大千.张大千先生诗文集卷三[M].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202.[48]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四僧书画全集·石涛[G].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442-451.[53]“自蜀人张善孖、张大千来上海后,极力推崇八大、石涛,搜求遗作,不遗余力。而大千天才横溢,每一命笔,超轶绝伦。于是石涛、八大之画始为人所重视,价值日昂,学者日众,几至家家石涛、人人八大。”见周积寅,耿剑主编.俞剑华美术史论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173[55]方闻教授的学术成长背景,参见谈晟广.“永恒”之山—解读方闻《〈夏山图〉:永恒的山水》[M]//方闻著,谈晟广译.夏山图:永恒的山水.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7-31.谈晟广.“回家”的“故事”[M]//方闻著.谈晟广编.中国艺术史九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7-24.[56]方闻著,赵佳译.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28.[57]方闻著,李维琨译.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17.
图文综合来源网络,分享此文旨在传递更多有价值信息之目的。和万千书坛精英,一起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原文不代表书艺公社观点、立场以及价值判断。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与书艺公社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