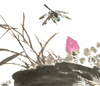阿巧
文/武夷学院2020级汉语言文学1班吴梦颖
春日的清晨总是在凉爽中带着冰冷的意境。树梢上的寒露滴落了,迎春花也张扬起来了。熹微的晨光和朦胧的雾影里,萧瑟的小城镇中,一群早起的人匆匆忙忙的,把热闹装饰在街上。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就是这个南方小镇上最平凡的一个早晨。而当熙攘的人群在清晨六七点钟才自在地流入大大小小的街道时,一条灰色的小巷早在凌晨四点就起床梳妆了。这条街巷与整个热闹的城市都不相干,它是这个小镇灰白色的一片影子,就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阿巧一样。
顺着一条浑浊的小河沿桥走,好像回到了四十年前的朴素生活——窄窄的石子路通往两条交叉的巷子口,从左看到右,没有电梯高楼,只有一栋栋灰漆漆的水泥墙造就的相同模样的建筑,这片建筑大多是四层,因此远远望去像一堵平齐的围城。小巷两边很窄,每一家门户与对面相距不过三米,轿车若是无意闯入,便在此地寸步难行。这里是一片没有新鲜感的境地,所有的房屋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成后,再无更改,一切都是老式的面貌,里面住着的,自然也是老式的人们。自建房群落处在这座城镇的最中心也是最低处,所有溪流汇集起的流水都顺着这一条小河倾斜奔涌。小河虽是顺势而流,水色却并不清明,水中占满红色的飘摇的水草,除了水蛇,三十年来从未见过另一类河中生物。不难看出,这是一片寂静之地,是这座城镇朝外哧哧呼呼吐着白灰的“烟囱”。
这条很陈旧的小巷被居民们平白地称呼为“老街”,老街里建着老式的楼房,住着上了岁数的老人。仿佛是共同约定过一般,老街里没有青年的人影。为了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年轻的子女全都外出打拼,留下年迈的双亲与还未独立的儿童作伴。房子里缺少了鲜活气,整条巷子便死气沉沉,没有生机。即使是再喜欢嬉皮笑脸的顽童,也在街巷清净无人的氛围中受到熏染,不由自主地变得安静老成起来,都将自己当作这片静地的倒影。
大多老人都愿意将多余的房间出租,以低廉的价格换来鲜活的人气,给自己省出一些打扫空房的体力来与邻居谈天说地。当然,低廉的价格也代表着并不便利的生活,有的屋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只能由几个租客合用一间厕所;他们所租的小房间也大多仅有十二平米,没有水池、冰箱和空调,一切吃喝由自己解决,还得与房东共用一个小厨房。这样艰苦的居住条件,要将自己像小鸟一样关在一个刚刚好呼吸的笼子里,在这个万物发达的新时代,没有几个年轻人愿意适应。因此,老街招不来年轻的活力。乐意“屈尊”入住的,除了昼伏夜出、只为了有个落脚的工人,还有被出去打工的子女从农村带上城里来,不知怎么照顾的孤老父母。阿巧就是后者中的一员。

阿巧的原名已经无从得知。她只告诉我,从前她的父母就是这么叫她,她的熟人也是这么叫她的。我与她熟悉后,嘴边喊她阿巧婆婆,心里却也开始喊她阿巧,以示亲近。当她随着儿子上城时,已有七十岁了,到了这样陌生的地方,再没有相识的人能喊她阿巧,隔着年龄的差距,我们小辈的都只叫她做“婆婆”。
阿巧的儿子四十多岁,只有领着阿巧来我家租房时出现过一次,他与我的奶奶将房价讨价到了两百元一月,包水电。就将阿巧安置在了我家一楼的一间空房里。
老人自上城的那天便带着一根拐杖,枯木一般的双手轻轻搭在枣红色的拐头上时,分不清是哪一个更显得粗糙。她浑身上下都是褐色的,像是烟叶烤好后的颜色,除了头发是灰白相杂的,都一丝不苟地用黑色的木簪子梳理好。阿巧穿着一件紫色的格纹衬衣,那是她唯一一件整洁的新衣服,这是后来两年我与她的相处中才发现的
与母亲一样身形瘦长的儿子像幽灵一样,将阿巧小小的行李包放到她未来几年都要相伴的木架床上,替她简单打扫了一下卫生,沉默地给了阿巧一个老人电话机,又发挥幽灵的习性消失不见了。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更多对这位中年人的印象了。
阿巧的年纪比我的奶奶还要大十多岁,因此得到了对待长辈的恭敬态度,我时常猜想,奶奶是否把对待已走母亲的孺慕也放在了阿巧身上,才会像个正值壮年的子女一样,在她的事上亲力亲为,时刻照顾。奶奶是个没有心眼的好人,她对待喜欢的人就一定温顺可亲,将对方的苦难当做自己的错处来愧疚,她对阿巧就是这样,于是生怕自己这个房东怠慢了客人。阿巧也是个好人,她是和奶奶相契合的伴侣,她懂得奶奶的付出。作为一片独在异乡的浮萍,也就更加在生活上依赖对方。可是好人总是没有报答的,两个同样善良的人在一起相处,总会有遭罪的一方。在后来的两年中,我充分地领受到了这悲剧的宿命。
在我们这样的局外人的眼中,阿巧无疑是可怜的。她那位将她从遥远家乡带到这座陌生城镇的独生子,是靠着卖力气来赚血汗钱的一介工人,吃住都在工地,从不来看他无人看管的老母。他的存在,在我的心中是一片羽毛般的重量,在阿巧的心中,却是她整个人生的支点。阿巧的儿子很喜欢购物,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购物癖,他的网购地址没有挂在工地,而是绑定了我家,因此每当快递员将他购买的东西放在阿巧的屋子里时,阿巧好像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知道儿子的状况。那批快递她从来不拆,总说那是儿子的东西。除了一日三餐外,阿巧没有任何娱乐的需要。她不认为儿子送来的东西是给她买的生活用品。因此,等箱子一个个堆积在角落里,她就把盒子一个一个地垒好,整整齐齐地摆放,从快递的数量来数她儿子离开的时间,也许这就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母子俩的交流方式。
可我们都认为阿巧的儿子不孝。他为母亲所租的廉价单间,曾经是我幼时和朋友玩耍躲避的补给点。那是一间没有电视的屋子,新贴的瓷砖地板蕴藏了整栋房子的寒气,真正做到了冬冷夏阴。由于回南天的潮湿水汽,天花板与墙壁的接缝处生出了大大小小的斑点。屋内的电灯还是老式的暖光灯泡,简陋地吊着一根喝醉了的电线,窗帘也是淡紫色的一层纱,比阿巧的紫色衬衣还要薄一点,隐隐绰绰地将窗台前枯瘦佝偻的人影展现在过路人的眼中。夜中,则有野猫神秘的嘶叫,到了凌晨四五点,便有邻居家散养的鸡鸣声把早起的老人唤醒,随之陆陆续续的摩托车的轰鸣声会嗡嗡地传到阿巧的耳中。此时她也醒来了,拿起奶奶热心分给她的不锈钢水杯和牙刷,在昏暗的日光中摸索到桌旁的拐杖,支撑自己蜗牛一般的小步子到公用的卫生间去。
我的奶奶比阿巧要起的早一些,四点时已经洗漱完毕,给她倒好一碗白粥,趁着清晨的凉意去市场买菜。阿巧慢慢啜了一口白粥,坐在大堂的长凳上看窄巷路过的自行车和上学的小孩。等到中午,阿巧就不知去向,奶奶本想继续给她装好餐饭,也找不到她的踪迹,认定她是自己出门吃饭去了,中午便不再管她,只在早晨多为她装一些稀饭和小菜,此后也一直如此。踪迹飘渺的阿巧在午后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发着呆度过一整个下午。
在我没有与阿巧熟悉以前,她每日都过着这样规律又无趣的生活。除了奶奶依稀能辨别她满口乡音的话语,耐下性子和阿巧交流以外,她在这个陌生的巷子里没有朋友。

和我的奶奶一样,阿巧没有上过学,不会识字。她们纯粹靠着感官和口语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生存,没有手机,更不会用现代电器,奶奶喜欢亲手洗衣的原因便在这里,她也从不用微波炉和烤箱那些需要记住使用步骤的器具,那对她们来说不是便利,而是精神上的磨砺。换句话说,她们只渴望拥有小小的一方生活天地,这个天地不需要有多么便捷的高科技,只需要她们的亲人还在可以接触到的身旁便心满意足。
我的奶奶不会使用电话,因此爷爷没有拆除家中唯一一台早该淘汰的红色座机,那是奶奶唯一会使用的交流工具,她只需要听到清脆的“叮铃”,放下手中的活计去话筒处发声,便可以与自己的亲人隔着遥远的时空相会。可阿巧不行,她已经太老迈了,眼睛也看不清远处的事物,还不愿带上老花镜。因此他的儿子与她的交流,全都只能靠着那一台平日默不作声的老人机。儿子告诉阿巧,只要电话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就点开一个最左边的按键,这样他们就能像是在家中一样交流。阿巧便只记得那一个按钮,那一个来电音乐,她知道这一台电话是她和儿子独有的秘密。
有一天,我和阿巧终于说了话,那是在月末,即将要结清阿巧三个月未缴的租金时,阿巧来向我搭的话。她依旧撑着她那根枯木拐杖,上面红色的油漆都已经脱落,慢吞吞地朝厨房走来,奶奶与朋友出门遛弯,便叫我留下看家,因此阿巧也只能找到我。她终于换了一件白色发黑的衣服,下身是不变的黑色长裤,一双老布鞋。因为寂寞而忧郁的眼角下耷着,一脸的苦相。我近距离地看她,越看越和奶奶她们的老态不一样。奶奶快六十岁,身体还很结实,凡事喜欢亲力亲为,肚皮鼓鼓也并不影响她身形的敏捷,而且总爱笑,没有忧愁的烦恼;奶奶的母亲在八十多岁时离开了,在此之前,我也见着太奶奶圆圆的身体和奶奶如出一辙,奶油一样丰润的脸庞,雪一样的白发稀稀落落,却显得很精神,嘴角不见人先笑,她俩都是弥勒佛的面相。阿巧是个佝偻着脊背的瘦个子,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生活无奈,身体像是在树皮上裹了一层干泥巴,才能把皱纹和粗糙的肌理表现的这样细腻。
我从前与太奶奶在交流时尤为不顺,她早已落光了牙,说话含糊,更听不清我说的话,我便练就了顺风耳与狮子吼,掌握了与老人交往的技巧。因此也就听得出阿巧来找我是为了什么——阿巧用她那一口不知名的家乡语音含含糊糊地叫住我,让我帮她打电话给她的儿子,仅此而已。她眼里是对我的绝对信任,和我遇见的每一位老人一样,认为当代年轻的小孩总是无所不能,充满力量。这样简单的事我自然能够帮忙,我仅是将手机解锁,打开通讯录里唯一一个的姓名并拨打,便让阿巧感激不已,因为她向来将手机当做一块不能丢、用不了的硬砖头,听到公共短信的系统铃声都引以为奇。
电话那头很快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阿巧向我道了谢,撑着拐杖又慢腾腾地走回自己的房间,边走边慢腾腾地让儿子回来一趟结清费用。我只把这当做那一日中一个无足挂齿的小插曲,谁料阿巧却为此向奶奶大夸了我一番。奶奶吃饭时笑她,朝我说:“人家说你是个好孩子咧。”自己的孙女被人夸奖,自然是让她容光焕发,且傍晚时分,阿巧的儿子回来交完了住宿费,让她的心情更加愉快起来。
阿巧也因为儿子来看她而高兴,拿着儿子给她从某次酒席上带回来的一盒糖果来找我。我和阿巧的年龄差了半个世纪还多,老人对与自己年纪相差极大的孩童总有着温柔慈爱的心理,阿巧看我也是这样。她总算不再握着那根掉了漆的木拐杖,而用一只细细的手抓着我的胳膊,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摇着头说“太瘦了,太瘦。”“多吃饭呀丫头。”将那视若珍宝的红纸糖盒拿给我,以我幼小的兄弟受了奖励后,兴冲冲地来向我讨表扬的期待眼神来看我。阿巧不知道工业制成的糖果放得太久会过期,她绽放的年代里,糖果还没有保质期的说法。她以为她给我的是最珍贵香甜的琼浆,却不知道自己那奉献的心情才是最令人动容的地方。我自然也投桃报李,回之以微笑。

老人比任何人都要善于读取情绪,阿巧知道了我也不排斥她,就总爱坐在大厅里晒太阳,等我出来时就能与她聊天。我不在的时候,奶奶便会陪她一起在大厅的长椅上面对面坐着,将大门当做椅子的靠背来枕着,两人摇着蒲扇,有时喂一喂前来觅食的野狗和野猫,聊一会天,一天也就清闲地过去了,两位老人结伴的生活没有波澜,比一切电子设备带来的娱乐都要快活。那是阿巧在这栋房子里过的最舒心的日子,足以将她眉头不散的哀怨驱走。我也在那一年的时间里了解了她家乡的故事,还有她自己过去的时光。
阿巧说,她的母亲给她取名字,本来是叫阿悄。因为她出生时就不哭,大人们用力拍她,打了好几下才哇了一声,让大人知道她没有什么毛病。长大后她也不爱说话,除了要干农活,都躲在家里,妈妈就说干脆喊她阿悄吧,这孩子总是静悄悄的。她爹说,阿悄不好听,寓意也不好,还是叫阿巧吧,我家姑娘生的乖巧。这名字就拍板定好了。
阿巧说,名字好不好也没什么用,她家里穷,没有上过学,从小只会干活。她最喜欢的就是干农活,家里的那一片烟叶地是她的乐土。当她站在阳光下干活,在斗笠的阴影里看地上自己长长的影子,她可以不和别人说话,专注着只做自己的事。等到金黄的稻谷又一次成熟了,家里为她找好了归宿。她很快嫁了人,和丈夫在邻村有了自己的小家。丈夫为了家里的生活很卖力地干活,自己也管着家里的农田,生活和没出嫁前一样。丈夫说过,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要好好读书,不能像他俩一样,大字不识,没有文化。阿巧相信他。可他们一共有过三个孩子,两个已在冬天夭折。二人对幼子更加珍爱,不再求他成才,只希望他健康长大。等到儿子二十岁,丈夫便也走了。初中就辍了学的儿子对阿巧说,农村的日子太苦了,赚不到钱。我要去外面拼一拼,娶个媳妇,让妈住城里的家。可儿子走了,阿巧便独自一人了,她只能随着儿子一起走,离开最熟悉的土地。
我听完便明白为何阿巧每日形单影只,奶奶为此也更加呵护怜惜她,有时亲热的做派真让我认为她将阿巧当做了母亲。
即使有了说话的对象,阿巧的生活依旧是苦涩的。奶奶对她再好,依旧不是她的子女,她心中想的依旧是那个成日干着苦力活的小儿子。可儿子还是不怎么给阿巧打电话,只有快递还在不断地送来,被阿巧成堆地摆在她房间闲置的沙发上。我有时想着去帮阿巧把快递全都拆开,看看那些是不是儿子给母亲寄来的想念,满足我的好奇之心。母亲倒是制止了我,让我少去多管闲事,于是这事不了了之。
我和阿巧日复一日地相处着,维系着良好的忘年友谊。奶奶也依旧当着慈悲的圣人,为阿巧准备一日三餐,让她不要去餐馆吃不健康的快餐,还时时刻刻关心她的身体,热情地想要帮人帮到底,便替她清洗衣服,连热水也要替她烧好。我发觉奶奶的好似乎有些开始过了线,奶奶却不觉如此,总说小小的事情能帮就帮,只是一些饭菜而已,总归自家吃完还是得剩下。爷爷也没有意见,因为他们都是善良过了头的大好人,认为好心待人一定不会结出坏的果子。
她们这样依偎着过了一整年,奶奶的无私付出让阿巧彻底依赖上她。帮助阿巧的过程是那样充实,这或许让奶奶得到了更加珍贵的满足感,整个人的兴致像皮球一样鼓胀起来,每天都充满了活力。我对阿巧却为此有些疏远了,因为在两人亲密的联结下,我察觉到了潜藏的火焰中有一根即将要烧断的蛛丝。
事情的开端在于二楼的一位租客的无理取闹。在半年未缴房费被我的父亲提醒了一回后,这位三十多岁的单身男子开始改变了作息,每日凌晨出门,零点回来,电话也总是挂机,刻意不让房东有向他讨钱的机会。等到有一天,我的父亲回来,好声好气地拿着账本与他对峙,男子嬉皮笑脸地告饶,说自己的工资也还没有结清,等到三个月后,保准一次性搞定。对待无赖,若是以君子的姿态,是讨不到好处的,我的父亲要做君子,自然是无功而返。到夜里吃饭,餐桌上大人们讨论起这件事,爷爷最终发话,人都会有难处,让他再拖欠几个月,今年年底一定要结清。我默默听着,为爷爷的话所震撼,也觉得是自己家人太过软弱可欺,才会导致这样的泼皮造次。我不打算容忍,更不想沉默,打算适时地开口展现我跃跃欲试的反动,母亲掐着我的手,终于用她的眼神制止了我。
奶奶第二日自然与阿巧谈到这件事,阿巧说,自己的房租也还没结,让我再替她打通那个手机中唯一的号码。事情却没有这样轻巧地揭过去,那一日发生的事情如水面轻轻荡漾的纹路,只是石子掷入水中激起的第一个微波,谁也没有想到后续的连锁反应竟有那么漫长。
阿巧的房费到了月末已经是第八个月了,阿巧让我打了好几通电话后,她的儿子姗姗来迟,却是为诉苦来的。阿巧怯懦地站在儿子后边躲闪着,两只手都攥着拐杖,老人核桃一样弯弯绕绕的皱纹像迷宫一样没有出路,两只眼睛呆呆地看着地面,不看奶奶也不看我。
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那也是一张苦相,却比阿巧要狡猾地多,从眼神中折射出市侩的臭气。从阿巧的口中,我向来听到的是她珍视的小儿子有多么好,她湿漉漉的眼睛中有着母牛舔犊的清澈之爱,我也由此认为那个早早辍学出来打工的剪影还是个纯善的孩子,显然阿巧错了,只有她还活在往昔的纯真年代。
那个“孩子”告诉奶奶,自己真的没了钱,暂时付不了房租。从母亲的口中,他知道奶奶一家都是天大的好人,希望能再讨一份好,将自己没有时间照顾的母亲托付给我们家。
当时是何种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阿巧的脸上麻木而羞耻的神情我却记了许久,因为奶奶同意了。男人心满意足,奶奶为阿巧免费提供了三餐,他便认为阿巧是不再需要用到金钱的,连一张小额纸币也没有留下,便喜气洋洋地走了。
阿巧也许是想自己攒一些钱来给奶奶,可惜她身无分文,毫无积蓄,连存折都不在自己身上。即使奶奶依旧真心待她,她此后面对奶奶时,也权当做是施舍来感恩。家里的气氛也变得危险了,因为阿巧呆在家中白吃白住了半个年头,长辈们却仍愿意做个菩萨救济,一些闲言碎语便在饭桌上流了出来。我虽还想一如既往地对待阿巧,阿巧却在那以后像一颗含羞草一样,见了我便紧闭起自己的心扉。
在这之后不久,那颗石子激起的水漂还没有消散。这一次发生的事情断送了我与阿巧的友谊,也让她成了众矢之的。
我曾预言说,奶奶和阿巧之间,总有一个好人要受到伤害,事情就发生在她们两人中间。为了替阿巧将她一时糊涂锁住的房门打开,奶奶从窗台上爬了进去为她开门拿钥匙,在过程中摔了下来,好在只磕破了额头。
当我回到家听到这件事时,奶奶已经清理好头上的肿包,朝我摆摆手,没有说什么。可试问哪一位有心肝的子辈在看见亲人受难能够无动于衷?
我不是圣人,那阿巧便成了我的仇敌。
我立志要隔离她,每次走出大门都目不斜视,即使对视,我也要让阿巧看见我眼中的仇恨和斗争。奶奶摔下窗台这一件事是如何发生的,我已经没有了探究的欲望,不论那是奶奶主动想的主意,还是阿巧稀里糊涂提出的。我只知道,我无法再支持奶奶无怨无悔的善良。家人对奶奶受惊摔倒的事虽默不作声,却也与我在同一战线——因为答应了照顾阿巧的请求,不能将她请出家门,便全然当做她是不存在的。阿巧的朋友只有我和奶奶,而我却离开了她,在阿巧的痛苦里,我热烈交织的情感在愧疚和大仇得报的愉悦之火中燃烧。
阿巧变得越来越沉默了,她最终也成为了这栋老房子里的一片单薄的影子。
受到了排斥,那么与阿巧的分离也是定论了。在某一天,这个住在小小鸟笼里的影子随她幽灵一般再次浮现的儿子离开了。离开前,阿巧的儿子付了一半的房钱,他承诺一定会回来还钱。不知为何,在那一天这个男子的市侩忽然被抹去了,他的眼睛里浮着疲惫的血丝,连话语都是沙哑的。

阿巧的包袱很小,她两年来没有买过衣服,总是节俭地穿着几件洗泛白了的旧货,两双一模一样的黑布鞋。连平日里使用的锅碗瓢盆也不属于她,那是奶奶分给她的,她并不打算带走。奶奶再次进入这间空屋子打扫时,那些堆积的快递盒子也被清空了,一切都回到了两年前的状态。奶奶叹息道:“这下子又要无聊了。”她以佛陀一般的真心悲悯着那个无意伤害了她的老妇,好似一眼就看到了苦难的最终结局。但她叹息完,还是和往常一样为家里打理上上下下,与相熟的老太太们在日暮去公园遛弯儿,白日里就养养兔子,喂喂野猫,照样能打发日子。
一片影子的离开看似没有造成任何影响,空出来的房间很快又住进了一位作息颠倒的工人。要说清冷,与以往没有阿巧的日子是一样的,这栋灰白的房子与老街上所有苍白的屋子都是一样的寂静,而生活也不会刻意为了某个人而停下脚步。奶奶有时还会对我提起那位老婆婆,想象对方的去向。
在阿巧离开的一个月后,才发觉我在想她,那些因为奶奶受伤而涌上心头的激情消退以后,我开始为她直面我的责难而难过。奶奶后来总是平静地看着我,没有苛责我对一位老人的冷漠,因为在这一件事上,分不清是谁对谁错。
阿巧消失在我生活中的第二个年头,奶奶以平常的口吻在饭桌上说着,阿巧死了。正如平地一声炸响的惊雷,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现实。
家人顾及奶奶对阿巧的怜悯,也表现出慈悲的姿态来,追问阿巧为何离世。奶奶将溅到手上的汤汁在围裙上蹭去,从裤袋里掏出一小叠百元现金,说是今日阿巧的儿子送了钱来。快五十岁的大男人鬓角全白了,本就被生活折磨过的脸色已经完全被风霜浸染,在奶奶如亲姐般温和的目光中痛苦地嚎哭了。钱是阿巧自己的积蓄,她在死之前的几日里,每日都嘱托儿子一定要把这笔钱还清楚。
我身体一时间冰冷地颤栗。
原来老人在两年前便病了,从突然的记忆紊乱到认不清人,到后来每日夜里为浑身的疼痛呻吟着。她原以为自己只是太老了,老得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也许是得了老年痴呆。就将奶奶当做了自己许久不见的孩子,还满心欢喜地认为对方终于有时间回来看她,让奶奶化作的儿子的影子像从前在乡下的家里一样,帮自己去做自己这幅老迈的身体无能为力的事情。
我见过亲戚家痴呆的老人,见过许许多多不同的身影。他们从前灵动的笑容和慈爱的眼睛,在某个未知的时刻被病症光临,从此再无记忆里的幸福。阿巧也得了这悲伤的病吗?我心里问着。
奶奶对我摇摇头。
在那一次错误之后的某日,阿巧的儿子也发现了母亲在夜里的痛苦,强行将她带去了医院。一个为人熟知的真理是,在你淋着暴雨正瑟瑟发抖,迎头再被泼一盆冷水是很寻常的。于是阿巧查出了癌症,这是她自己暗中预料到的苦难。
总是冷漠的市侩儿子撑在墙上的手也无力地掉落了,把所有吝啬的面具都丢了。他和母亲说:“一定会有希望的,它能治好的,不管多少钱,咱一定治。”阿巧不想儿子花钱,她知道儿子这么辛苦地在工地卖力气是要拼了命在城里买一套房子。儿子曾经说过,要在城里有个家,再娶个媳妇,把娘接到城里的家来享福。母亲到了城里,并不觉得城里的生活比遥远的故乡要幸福,儿子快五十岁了,还是娶不到媳妇。可她想看着儿子实现自己的诺言过上幸福的日子,起码该有套房子。自己已经活得够多了,她不能让儿子动那一笔买房子的存款。
孝子的眼泪在父母的眼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父母一生中最无法割舍的莫过于他们亲手养育大的幼苗。阿巧还是以危险的高龄上了手术台,儿子说,一定要治。母亲再走了,他就真的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做孤家寡人了,要房子还有什么用。
阿巧是幸运的,她的手术成功了。
儿子听从了阿巧的话,送她回到了乡下老家修养。自家的农田早已在进城时转手了,她却在休养后感到自己像年轻时候一样有力量,总爱拄着拐杖去别人家里的地上转悠,有时还能搭一把手。这里是阿巧最熟悉最深爱的土地,她知道自己是离不开这个家的。儿子也打算把城里的工作辞了,回到村里去继续干农活,阿巧不许他回来,让他要为了许诺给母亲的幸福继续努力,少去沾染乱花钱的那些坏毛病。
儿子离开了,阿巧便成天悠闲地坐在家门口的小石凳上发呆,闲极无聊了,便去田里转一转。她一生都是这样过来的,到了七十多岁,还有什么不适应呢。
她一生的心愿都牵挂在儿子身上,只有一件事让她难以释怀,那就是儿子使坏赖掉的那笔账。她知道儿子是一时给鬼迷了心窍,自己却无法当初原谅躲在别人身后默默看着的自己,那对不起她承过的恩和情。
阿巧叫儿子把钱取出来了,她记得数目,还差人家整整一千元,一定要儿子去城里带给照顾过她的好心人家。儿子能有什么不答应,发誓自己一定还会带去母子二人的感谢和歉意,她这才心满意足地笑了,将最后一件遗憾打消。
老人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打算悉听天命。

阿巧的人生就像一部庸俗的悲剧,丧子、守寡、癌症;也是一幕乱了套的话剧,感受到了温情却又让它失去,被人鄙弃又得以洗清冤屈;更是一场即将要说再见的电影,承载着许许多多的离别与遗憾。
不论他人如何评说阿巧的故事,它总归已经到了尾声,这个故事里不再有我和奶奶的身影,因为我们都只是她人生七十多年旅途中的平凡过客,儿子也只是阿巧的道路上的一条长河,这条河流绵延不息,滚滚奔流,道路却总有走到尽头的时候,那是阿巧漫长旅途的结局。
阿巧人生的最后我并没有参与,但我也能想象出,这位老人在最后的时光里,摸索在烟叶地里佝偻的身影,还有她感受着梦幻的阳光再次和煦地照到她带着斗笠的身体。在母亲般呵护的温暖日光中,她闭上眼睛,整个溶化在了光里。
编辑|郑宇情
校审|魏维 叶雨湘
联系客服

微信登录中...
请勿关闭此页面